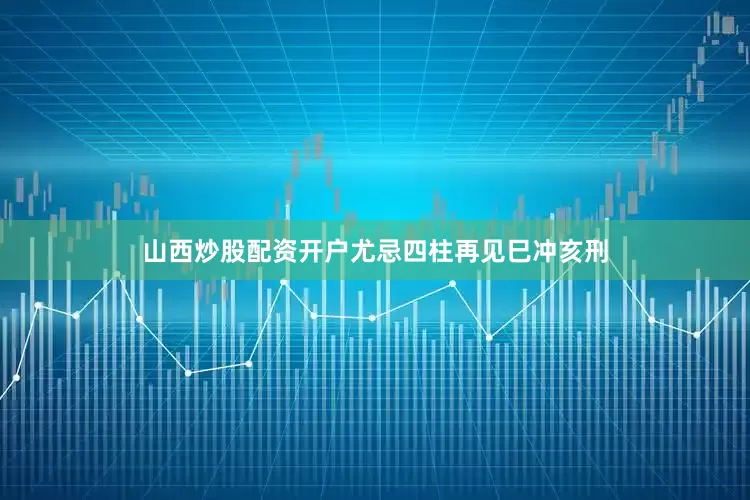■ 陈公炎
晨光微熹,尖峰山敛去往日峭拔,化作宣纸上洇开的半阕淡墨,峰峦隐入烟霭,似仙人遗落的笔锋。檐角铜铃濡了湿气,叮咚声便沉作古琴泛音,一音一颤,皆是未醒的梦呓。
这便是婺州城入梅的韵脚了。
记忆里的梅雨时节,婺江总褪去温婉的纱衣,露出狰狞的底色。但逢三日连阴雨,上游山洪裹挟泥沙奔涌而下,江水便浑如滚沸的黄浆,浮沫中翻卷着断枝、泡沫箱与碎玻璃,在通济桥墩处绞出深褐色的漩涡,浊浪拍岸时,腐叶与塑料袋黏结成块,随波沉浮如溃烂的痂痕,将古子城一段江面腌渍得满目疮痍。
桥头茶肆的老茶客们抿着陈年普洱,摇头叹道:“这般浊流,怕是要逼得易安居士撕了《武陵春》的诗笺。”话虽戏谑,眉间却凝着无奈。
最煎熬的,是临江而居的百姓。梅雨如注时,青砖缝里渗出黏稠的黄浆,墙根泛起墨绿的霉斑,像一簇簇毒菌在暗处疯长。晾晒的蓝布衫终日挂着水珠,取下时总沾着股腐殖土的腥气,连枕边的竹枕都洇出斑驳的盐渍。孩童们不再去江边捞蝌蚪,妇人洗衣槌的闷响也沉寂了——唯余浊浪昼夜拍打石阶,将“细雨鱼儿出”的诗意,碾作“浊流垃圾漂”的荒诞。
改变始于那年惊蛰的雷声。
展开剩余54%工程队施工的轰鸣最先刺破古子城的暮气。他们如匠人般俯身,将错综如乱麻的地下管网重新捋顺,让百年淤塞的“血管”重新搏动——混凝土裂隙间涌出的不再是腐臭的浊流,而是逐渐清亮的脉搏。
治理的巧思藏于毫厘之间。江北,芦苇的根系在生态滤池中编织成翡翠色的滤网,水草与贝类共生为天然的净水工坊;江南,智能分流井的电子眼如鹰隼般锐利,暴雨将至时,闸门便以秒速切换姿态,将狂躁的江水驯化为温驯的琴弦。
如今的婺江,虽在梅雨季仍裹着半面轻纱,却自有一种洗尽铅华的清朗。水面澄明如鉴,不见半片浮滓,唯余两岸的仿宋骑楼浸在水中,青砖黛瓦被涟漪揉皱又熨平,恍若一卷徐徐展开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墨色未干,已染尽江南烟雨。
打伞的姑娘赤足涉过浅滩,惊起白鹭数点,羽翼掠过花海,抖落一地鸢尾的碎星,恰与六百年前易安居士笔下“水通南国三千里,气压江城十四州”的苍茫意境,在暮色里悄然相契。
雨歇的黄昏,我伫立通济桥头。夕阳将江水淬成熔金,几叶晚归的扁舟正犁开镜面,橹声欸乃间,细浪碎作粼粼的笺纹。
夜鹭振翅掠水时,我恍然懂得:这一江清流,何止涤尽往日浊痕?这清波的源头,一半是沙畈水库的雪浪,一半是万人掌心磨出的茧花。
这江水已将易安的愁思、宾虹的墨痕、光南的弦音,一并酿成流动的史诗——它淌过孩童课本里的水墨插图,漫过游子枕畔的归舟残梦,终将汇入历史长河,化作古子城茶肆那副褪色楹联的注脚:“一江水养一方人,千年城载千年梦”。
发布于:北京市配资炒股官网开户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